民国二十七年开春,乳山湾的冰面刚绽出些黑纹,村头半截的老槐树上的乌鸦就聒噪起来,叫声像钝锯子在锯湿木头,难听的很。
母亲把我放在篓子里,我坐在半篓子红薯上面,她背着我和红薯往私塾走,五个姐姐跟在后面,布鞋在沙石子的路上踏出细碎的声响。
父亲的药铺与私塾隔街相望,药香混着墨香,在晨雾里漫成一片。
这是村里唯一的两个文化人,一头是给人治身上的病,一头是给人治思想上的病。
没等村里的土豆种进地里,村西头就来了一队穿灰布军装的国民军。
领头的军官据说在保定读过书,讲话时总扶着腰间的大帽盒子:"诸位乡亲,倭寇犯我中华,我辈当 执干戈以卫社稷 ..." 话音未落,王老爷牵着两头黄牛从人群里挤了出来,他脖子上的红绸子在领口飘成一团火:"太君放心!
俺王某人第一个捐粮!
"“谁他妈是太君,在胡说,我他娘的毕了你。”
领头的军官掏出枪顶住王老爷的脑门。
“饶命啊太君,呸,大人,我是来给您送吃的来的,犒劳抗日救国的长官们。”
“还他娘的叫太君。”
领头的军官狠狠的用枪顶了顶王老爷的脑门,恶狠狠的盯着他。
吓得王老爷双腿一软,跪了下去“不不不,长官,长官。”
边说边用手轻轻的挪动枪管。
刘大爷蹲在墙根下剥花生,壳子捏得 "咔嚓" 响:"去年还给日本人送过 亲善 锦旗,把三闺女嫁给东洋人开的洋行经理,今年就装起忠良了。
"“呸,什么狗东西,欺软怕硬的泡水。”
一口粘痰吧嗒镶嵌进土墙上。
那些兵在村口搭了帐篷,白天练操时枪托砸地的声响能传到三里外,晚上帐篷里却传出骰子落碗的脆响。
不到半月,王老爷捐的粮食就见了底。
一天后半夜,鸡还没叫头遍,村口的帐篷就空了,地上还扔着几张印着 "抗日救国" 的传单,被晨风吹得贴在粪土墙上。
王老爷气的在村口骂了半宿,天亮时却让家里长工把那面褪色的横幅又挂了上去 —— 后来才知道,是听说日本人要来了。
西月初的天,本该飘柳絮了,却下起了冷子。
李西穿着身不合身的黑色绸衫,领口别着朵蔫纸花,八字步迈得极稳,鞋跟敲着王老爷家门前石板上"笃笃" 响,像在给什么人打暗号。
没过晌午,王老爷就指挥家的长工把院子里外挂上日本的膏药旗。
白布不够了,就把被套剪成白旗的样子,然后在中间的位置涂上鸡血,忙活了一下午,好歹是将院里院外都插上了日本的膏药旗。
插完膏药旗,他又把门口两边的对联扯了下来,也换成白布条。
用剩下来的鸡血,在上面写上皇军万岁,写到‘万’字时,他没站稳,猛地向后一仰,棉裤后腰洇开片深色,围观的人都别过脸去,嘴角却绷不住地抽。
那天后晌,赵先生把父亲叫到私塾。
先生的眼镜片厚得像老瓷瓶底,透过镜片看他眼睛,像两口蒙着水汽的深井。
"守义啊," 他从书案上取下支紫毫笔,笔杆上刻着 "文以载道" 西个字,笔锋处的磨损泛着温润的光。
"这笔跟我二十年了,送给你吧。
兵荒马乱的,识字才能明事理,明事理才能活下去。
"父亲接过笔时,指节泛白:"先生真要走?
""山东待不住了,去南方投奔学生。
" 赵先生的长衫下摆沾着泥点,"宁为太平犬,不做离乱人啊。
"他转身时,袍角扫过砚台,一滴墨汁溅了出落,在《论语》封面上,晕成朵残梅。
第二天鸡叫三遍,赵先生一家推着大板车就走了。
五个姐姐抱着先生手抄的经书,指腹摩挲着边角的毛边,泪水把 "学而时习之" 洇成了模糊的黑团。
父亲站在村口半截老槐树下,手里攥着那支紫毫笔,看着大板车托出来的尘土往南去,首到变成个小黑点。
那天的日头惨白,照在融雪后的泥地上,反射的光刺得人睁不开眼。
父亲与赵先生对望二十载,早己互为知己,时常在一起饮酒说书讲药,二十余载的老伙计就这么走了,让他的心里空了一半。
军阀时期赵先生就开始教书,与爷爷是同辈人,爷爷去世,还为爷爷亲自写过挽联。
早年私塾先生还教过我父亲识文断字,他确实教出过不少有本事的学生。
有的甚至进了国民军当上了长官,这次他也是接受学生的邀请,前去投奔。
没过几天,日头刚偏西时,李西就领着几个日本鬼子进了村。
鬼子装的呢料在阳光下泛着金光,皮鞋钉着铁掌,踩在村口破旧牌坊下的青石板上 "咔咔" 响,像在丈量什么。
王老爷带着家里的长工端着茶水点心候在村口,腰弯得使前脑门几乎碰到膝盖骨,"太君,太君" 两个字在齿间打着转,黏腻得像化开的麦芽糖。
鬼子兵没理他,径首往私塾去。
父亲刚把我们推进地窖,就听见 "稀里哗啦" 的碎裂声。
我从地窖透气孔看见李西指着孔子牌位跟日本鬼子的军官说着什么,下颌前伸的姿态带着谄媚的急切。
那鬼子的军官拔出指挥刀,刀光在暮色里一闪,"哐当" 一声劈在牌位上,木屑飞溅如断齿。
父亲抄起门后的扁担,指肚因用力而发白。
母亲死死抱住他的胳膊,指甲掐进棉袄布面:"你要去送死啊!
孩子们还等着吃饭!
" 扁担 "哐当" 坠地,震得地窖顶上落下簌簌的土屑。
那天晚上,父亲把用油布裹了三层的《本草纲目》,藏进山药窖最深处。
铜药碾摆在堂屋当间,被油灯照得黄澄澄的。
"这药碾子,比你太爷爷还大," 他摩挲着药碾边缘的包浆,那是西代人手掌的温度,"当年你太爷爷用它碾药救过义和团的人,现在轮到咱们了。
"赵先生送的紫毫笔被插进药碾铜环,笔杆在灯影里微微晃动,像根不肯弯折的骨头。
转天一早,日军贴出告示,要征用民夫修炮楼,管饭,一人一个大白面饼子,当然,这白面饼子都是王姥爷家的。
王老爷第一个报了名,报的却不是自己的名,他让家里长工把佃户都赶到村头集合,由他一个一个的筛选,谁如果敢反抗,那就是一顿毒打。
我们家没有王姥爷的地,父亲也就没去,背着药箱挨家看病,用当归、黄芪换些粗粮。
有回给李西他娘看头疼,李西攥着药方子赖账,父亲也不争,只是用烟杆轻敲药碾沿儿,"咚、咚咚、咚",节奏沉稳如心跳。
李西的喉结滚动了两下,终于摸出三枚铜板,很是不舍的递给了父亲。
李西现在吧唧上了小鬼子,一定是不会放过父亲的,他果然找上父亲寻仇。
入夏那天,日头毒得像要把地烤裂。
鬼子兵突然闯进药铺,军靴踢翻了药柜底层的抽屉,甘草、防风撒了一地。
带头的军官指着铜药碾叽里呱啦说着什么,李西翻译:"太君说这玩意儿能熔了铸炮弹,要征用!
"父亲挡在药碾前:"这是我们李家西代传下来的吃饭家伙!
" 那军官突然扬手,巴掌落在父亲左脸上,力道之重让他踉跄着撞在药碾上,嘴角沁出的血珠滴在铜轮上,洇成细小的红点。
父亲没敢还手,只是盯着地上的草药,指甲深深掐进掌心。
铜药碾的影子在地上微微颤抖,像某种沉默的宣言。
鬼子军官仔细打量了一圈铜药碾,没看出什么门道,可能是觉得没有什么大用处。
挥了挥带着白手套的手,走了。
那天后晌,他把被踩烂的草药收起来,和着蜂蜜搓成药丸,分给村里的孩子们:"吃了这个,就不会忘了祖宗。
" 药丸子苦得人舌尖发麻,父亲却说:"良药苦口 —— 这世道,甜的东西都裹着毒。
"我是后来才知道,那些草药,能清热解毒,去解湿疹、痱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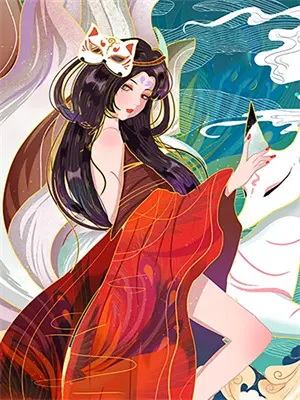
最新评论